未曾出版的书稿 让我成为《体坛周报》最忠诚粉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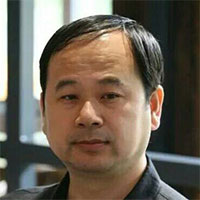
《体坛周报》创刊三十年,编辑约稿让我聊一聊自己和《体坛周报》的故事。拖了好几天没有下笔,不是没有东西可写,而是可写的东西太多:
1988年《体坛周报》创刊的时候,正是18岁的我在大学中开始认真踢足球、喜欢足球的时候; 2018年,我已经从《体坛周报》的普通读者,经过《体坛周报》最忠实的读者、作者、特约记者的磨练,成为了体坛传媒俄罗斯世界杯报道团的一名正式成员。
弹指三十年,中国已经从纸媒时代经过PC互联网时代之后,跨入了移动互联时代,变化极大;《体坛周报》也从简单的一张报纸,发展成为了多领域多方向前进的体坛传媒集团,故事极多;而我,也从一名军校大学生成长为一名中校军官,接着又转型成为了一名职业体育写手,感慨极多。
三十年的变化,三十年的故事,三十年的感慨,想在一篇文章中写就,真的不知道如何下笔了。
作业肯定是要按时交的。于是,我试图用情报学中最简单的概括归纳法来解决这个问题:寻找一个关键词,来形容《体坛周报》为什么三十年来能够一直对我拥有魔法般的吸引力。
方法对了,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因为,无论是大学中看《体坛周报》的时候,还是后来手持《体坛周报》的名片报道北京奥运会、里约奥运会、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,甚至平时想到每一位《体坛周报》的朋友时,我头脑中回荡的只有一个关键词:专业!
三十年,《体坛周报》不变的是对体育新闻的专业态度;三十年,我不变的是对他们这份执着的敬佩。所以,就写写自己因为“专业”而与《体坛周报》结缘的故事吧!
作为八十年代中后期“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”中的一员,进入大学好久之后,有了标准的足球场,更有了可以挥霍的时间,我才真正体味到了天下第一运动的魅力——随着1990世界杯的渐行渐近, 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书、即将升入大学四年级的我,成为了标准的伪球迷:由于自己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真正喜欢上场踢球,而且在场上踢人的时候绝对比踢球的时候要多,所以,本人对足球的技战术那绝对是不懂的;不过,由于自己的专业是信息搜集,而且学院图书馆里的外文资料那是相当的多,因此,对外国球星的轶事那是非常了解的,尤其是有关马拉多纳和荷兰三剑客的一切!所以,对外国球星绝对比对中国球星兴趣大,这一标准伪球迷的特点,在我的身上那是相当明显的。
敢于自称伪球迷,自然要尽量多的了解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星。学院的外文资料虽好,但毕竟全部是英语的,对于我一个学俄语的大学生,那还是有一定难度的,因此,看国内最新足球报道就成为了一个业余爱好。记得那个时候,国家体委办的《中国体育报》虽然也写足球,但专业写足球的报纸,却都是地方性的报纸:广州有《足球》报、天津有《球迷》报、长沙有《体坛周报》。
学院的图书馆里只有《中国体育报》,专业的中文足球报纸,就只能是到南京市里的报摊上找了。还好,那个时候报纸的价格也就等同一支冰糕,才几毛钱,对于我们这些每月有几十块钱津贴收入的未来军官而言,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支出。可是,想及时买到最新的报纸,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: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,报摊上的报纸,都是老板自己出钱订阅的,那是要占压资金的。所以,这种体育类的报纸,每个报摊道通常也就十份左右。也就是说,如果去晚了,报纸就没了!
在所有这些足球类报纸中,最难买的就是长沙的《体坛周报》!因为,与我同龄的很多南京地方大学的学生,那是翘课都要去买这张报纸的。
现在,已经记不清第一张《体坛周报》是什么时候读到了:有可能是在南京报摊买到的,也有可能是在同学马德兴那里看到的——他很早就在给各家足球类报纸写稿,所以他那里有很多足球类报纸的样刊。
不过,现在肯定记得《体坛周报》的第一印象:版式工工整整、文章凝重无比。说实话,第一次拿到《体坛周报》,就被其形式和内容吸引了:虽然足球吸引我的是速度和激情,但在读足球报道时,我却喜欢那种无数细节和数据堆砌在一起的内在逻辑,简单地说,我喜欢《体坛周报》的专业深度。
在《体坛周报》的伴随下,在军校学员队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下,意大利世界杯成为我了解世界足球的第一个立体窗口:各国球星奔跑穿越之时,身后留下的却是《体坛周报》为他们印上的文字之影。
91年军校毕业之后,可供自己挥霍的业余时间更多了。于是,经过92年欧洲杯丹麦童话的洗礼,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,成为我人生中最疯狂的一届世界杯:白天随手翻翻《体坛周报》,熟悉一下各路明星的最新动态,晚上则一瓶啤酒、一桶方便面、两根火腿肠,坚持看完三场比赛。结果,那届世界杯所有52场比赛,我是场场不拉:即使美国队与瑞士队之间的小组赛,号称了那届世界杯上最无聊的一场比赛,但我仍然从中找到了查普伊萨特与拉拉斯对抗的快乐!而这种快乐,大部分是通过阅读《体坛周报》之后,因为熟悉各路球星才拥有的快乐。有趣的是,2018年世界杯期间,我竟然在莫斯科红场边上的四季饭店里邂逅了拉拉斯,但无论如何,却也不能把那个曾经的山羊胡小伙,和眼前俊俏的中年人联系到一起了。
九四年美国世界杯,疯狂的不止我,疯狂的还有因职业联赛开始后疯狂的中国足球——不仅遍地开始出现足球学校,足球媒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渐次冒了出来:央视开播地体育频道,中国足协出了《中国足球报》,北京有了《北京足球报》,辽宁有了《球报》,甚至河北都有了一份《体育生活报》……
之所以对这些现在已经消失了足球报纸那么熟悉,只是因为,我当时已经不满足于只当一个足球看客,我想让自己的想法也变成铅字。 独自看球对于一个球迷而言是痛苦的,而对于一个会码字、会翻译的球迷而言,不让自己的见解变成铅字,也是痛苦的。因此,我与足球相关的文字,相继出现了《北京足球报》、《体育参考报》、《体育生活报》上……
是的,我没敢给《体坛周报》投稿。因为,我认为他们太专业了,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笔力可以所及的!毕竟,每次扫一眼《体坛周报》头版的标题,对于我而言,都是一个体味中国文字之美的机会。
1995年,随代表团在国外学习数月,偶然得到了一本俄国人出版的加林查自传《绿茵场上的小鸟》,细读起来非常有趣,于是回国后,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出来,成稿大约八万多字。
手中有了《绿茵场上的小鸟》的译稿之后,我决定按顺序给《球报》、《足球》报和《体坛周报》打电话,咨询投稿事宜。当时,我没有给《球迷》报投稿的打算,因为,我认为那里是老同学马德兴的势力范围:在大学的时候,马德兴同学就已经是《球迷》报非常欣赏的著名体育写手了。记得大四的时候,普通人的工资也就百八十块钱,但他已经花费七百多块人民币订阅了N多国外的足球资料了。他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伪球迷,所以,学院特批给他的一间小体育资料室,我是同学中唯一可以随便出入的。
我先打的《球报》的电话,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,她很是随意地告诉我,这是办公室的电话,你要找的应当是编辑。她说的很对,那确实是办公室的电话,因为,我在电话中听到了旁边人嘻哈聊天说话的声音。
我没有找《球报》编辑部的人,直接挂断电话后开始打《足球》报的电话,接电话的应当是一位男士,他一口的官腔,所以,没等他对我的描述产生厌烦,我就主动挂断了电话。
打《体坛周报》的电话时,我已不报什么希望了:我眼中最需要内容支撑的报纸都不要我的内容,《体坛周报》这么专业的报纸,应当也不会对我这个菜鸟手中的加林查——这位绿茵场上的小鸟——感兴趣了。
然而,柳暗花明处,真的会有峰回路转一说的:一位李姓编辑接的我的电话,在耐心询问了译稿的一些细节以及我的简要信息之后,他决定让我先把稿子寄给他看看,如果质量还可以的话,可以考虑在《体坛周报》所办的《射门》杂志上发表。
我兴冲冲地到邮局把一大包手抄稿寄往了长沙:那时还没有电脑,也没有邮箱,所有的稿子都是手写的。
然而,还没有等到译稿发表,我就接到了再次出国的任务,这一走一回,基本上就消耗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。期间,我间或得知:由于联系不上我,更由于《射门》杂志停办,《绿茵场上的小鸟》并没有发表。不过,幸运的是,即使在国外学习的时候,我偶尔也能读到《体坛周报》:上级会定期给我们这些长时间在外学习的年轻人发来一些中文书报,而负责此事的人员当中有位体育迷,他竟然会把多期破旧的《体坛周报》也随着一堆期刊杂志、书籍一起让人带到国外!而我自己,由于身处国外,不仅随手就可以买到俄国人出版的专业足球杂志及书籍,偶尔还能接触到俄罗斯军方专业的足球人士,因此,看到足球方面的长效选题——历史性的趣味故事,我就会在业余时间随手翻译出来,用国际平信的方式寄到长沙……至于文章发没发表,我是不在乎的:翻译文章寄往长沙,是我向自己最喜欢的专业报纸致敬的一种方式!

